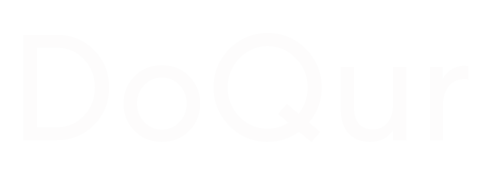素媛案原型犯人趙鬥淳獲釋:“他沒有被重判”,為什麼會激起公憤?
即使在許多國家的確是沒有“有罪”的,而且做為“其三”的象徵意義來說就變得尤為重要。很多人憂慮“社會輿論審判”會干擾“流程公義”,這方面只不過必須足夠多的開放才好,即使懲處原本就分倫理的和法理的,法理假如無法完全釋放公義,那么倫理就必須快速補位,這本身是不對立的。
所以,就現階段的基本共識來說,“性侵幼女”的犯罪行為“要重判”是最普遍的聲音。即使我們都清楚一個事實:“假如我們無法保護我們的小孩,自然我們的社會也是沒有希望的”。於此,對於“性侵案”來說,“性侵幼女案”肯定要被單獨拿出來看待的。
說實話,在大是大非面前,假如總是特別強調理智構築,特別強調放下屠刀,這可能將是對受害人的“二次凶殘”。我們有理由堅信看完影片《素媛》的人,都可能將想讓趙鬥淳速死,即使做為正常的人,是難以容忍禽獸般的惡人繼續活下去的。只可惜,趙鬥淳還是被刑滿釋放了。
就以我們國內的新聞媒體社會輿論對“素媛案”的關切程度上看,並並非說國內就沒有相似的性侵案出現,而是當我們藉由影片《素媛》更加清晰地看見性侵行為對幼女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時,總覺得“趙鬥淳們”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人類文明就可以在文明之馬路上更進一步。
當然,我們嗎希望12年的牢獄歲月能對他有洗禮促進作用,他說他們不記得犯罪行為時的情形,還則表示“想要跟受害人見面”,這看上去有思考的影子。但是對於見不見來說,決策權必須在受害人一邊,而非是侵害者想什麼樣就什麼樣,即使這也可能將是趙鬥淳的假心假意,而且不必太過在意。
即使我們在評估危害性的這時候,肯定要考量“被害人的年齡”,而“被害人的年齡”常常會決定她(他)對於侵害行為的承受力。此種考量的存有是基於現實生活傷害程度來說的,而非是把性侵行為分級化。要曉得,就性侵行為來講,不論是從倫理層面看,還是從法理層面看,都是罪大惡極的。
儘管在新聞媒體的攝影機下,我們能看見公憤四起,但是在韓國固有的法理體系下,對趙鬥淳的懲處也只能到此為止。日本的加藤詩織把他們做為“公義實驗品”,道盡“日本之恥”。而影片《素媛》隨著趙鬥淳的歸來,必定也會成為“韓國之恥”。
就“其一”的促進作用來說,這必須是有目共睹的。不但對日本的法理體系有觸動,對其他國家的法理體系也會有觸動。即使就公義的訴求來說,對於歐洲各國來說必須是無差別的。不過就“重判”的尺度來說,不排除歐洲各國之間存有一定的差異。
這件事情不但當年在日本範圍內引起公憤,甚至在許多年後,仍然屬於日本社會輿論球場上不可不提的“日本之恥”,這一點上從影片《素媛》的祭出,也能或多或少看見其中的抨擊和思考。與此同時,伴隨著全球範圍內反性侵思潮的崛起,“素媛案”也成為很多國家反性侵的典型啟蒙案例。
即便對於“素媛案”的社會輿論博弈來說,已經遠遠遠遠超過“重判”的象徵意義。甚至較之讓趙鬥淳速死,長久瀰漫在他身上的“社死”氣氛更讓他無所適從。這些看上去非理性的圍困行為,之而且被答允,就在於所有人都知道那是趙鬥淳罪有應得的結果,而且並不唐突。
除此之外,許多人憂慮68歲的趙鬥淳會繼續作惡,此種機率有多大嗎不好說。但是,對於此種心性暴虐的人來說,最好還是多加註意。許多這時候,犯錯者的懺悔不都是良心發現的結果,也可能將是為“趨利避害”做出的基本立場,而且該提防還是要提防的。
因而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做為日本的“素媛案”,能頻繁地步入我們的社會輿論場,這就在於樸實的公義裡,是沒有邊界線之分的。即便就“性侵案”的量刑,歐洲各國也是一直在探索,更何況“性侵幼女案”屬於其中的分支,更是會陷於這種邊緣化。
影片《素媛》伴隨著原型犯人趙鬥淳刑滿獲釋,再度步入社會公眾視野。在一定程度上,“素媛案”不斷在影片和現實生活之間交替發生,就在於近些年來,全球範圍內對性侵案愈來愈關切。回溯到2008年,素媛案原型犯人趙鬥淳殺害並性侵一位8歲的中學男生,並致其傷殘,但檢察官認定其“年齡大並且醉酒思想不穩”,加上當時日本刑期上限的法理明確規定,最後趙鬥淳僅被判刑12年有期徒刑。
不過就“素媛案”來說,假如並非影片的推波助瀾,可能將並不會引起如此大的關注。但這兒還是要從三個層面去看待:其一,讓此案不斷地步入社會輿論場,會促進有關法理的逐步完善,最起碼從公義的訴求上看,有非常大的重要意義;其三,即便當前的法理無法把犯人重判,但是社會輿論審判總還是可以讓其感受“社死”,也算補充性的一種懲處。
所以,在“重判”的問題上,可能將很適宜一句話:“心靈只有一次,要給與犯錯的人更多包容”。可與此同時,在面對不容復還的遭受時,這些正在刻畫心靈力的小孩,更須要的是另一句話:“心靈只有一次,堅決不容許受到任何侵犯”。
Tag 素媛
This site is a comprehensive movie website about movie posters, trailers, film reviews, news, reviews. We provide the latest and best movies and online film reviews, business cooperation or suggestions, please email us. (Copyright © 2017 - 2020 920MI)。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