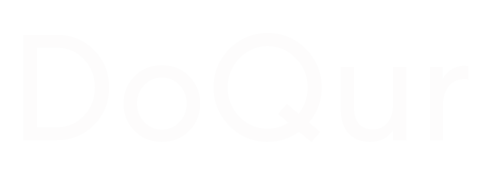最無趣的劇情片,拿遍了大獎
同樣的時空、同樣的事情,若是發生改變它的一些細節或轉捩點,情感的結局會什麼樣?
“我更喜歡直接在攝製的地方寫。我通常先選擇攝製地點,故事情節隨之而來。
(儘管自己有職業、有家庭,但基本只存有於談話中,沒有實際展現出它們),對偶然相戀的男人戀戀不捨;
金基德總是用暴力行為、性衝動來呈現出底層的苦悶、羸弱和抵抗,而洪常秀從不在影片裡去想那些問題。
自己總是在短暫的時間裡,快速愛上一個男人,毫不遮蓋地展開追求,最後又戛然而止。
洪常秀曾在專訪中說到他們寫電影劇本的習慣:
後來,我在生活中碰到兩個同愛洪常秀影片的好友。
即便是很日常的溝通交流,也常發生人物在一些場合
吵過之後,風平浪靜,迴歸冷靜。
我們極少有機會認真觀察生活裡的人,更沒有機會去深入探討劇中處理的這些頭疼的情愛故事情節:
他還在比利時愛上了佈列松的影片,自學了他的簡約和自然的藝術風格。
雖然是日常生活重現,但男女主人公的穿搭十分有模特兒範。
([玉熙的影片]);
出遊,是洪常秀的影片反覆發生的故事情節:
在金基德的回憶錄裡,他的人生充滿著了苦澀,家境貧寒貧困、母親嚴苛,小學
說到身世,不得不提與洪常秀同齡的知名日本編劇金基德。
編劇用脫離了職業環境的人做為他觀察感情的實驗品,用簡約的圖像詞彙和故事情節,沉積複雜且不斷高漲的情緒。
即便,從傳統倫理道德上看,出軌、偷請、師生戀、豔遇,都無法被直觀歸納為真愛。
金敏喜之後的洪常秀影片裡,所以也存有此種迴避,但主人公更多是在找尋感情滿足,甚少直面倫理道德困局;
獨有的視聽詞彙、敘事形式、人物設定和感情走向,已經是他的影片固有的風韻。
現如今再看,洪常秀的影片絕非晦澀,而是太直觀了,我們總覺得裡頭暗藏深意。
酒同時也是對立的催化劑。
自己總是出沒於酒吧、咖啡廳、近郊,或者一起出遊,和日常的熟人社會脫離。
1996年,兩人都順利完成了成名作,後來又都和主流電影業相悖,保持廉價創作。
假如把洪常秀的影片看做是一種感情實驗,那么他最常見的實驗設計是重複故事情節和內部結構。
這讓他能更為倚賴女演員的臨場演出,不須要在殺青前做過多場景準備。
正如李安說他看英格瑪·伯格曼影片時的體會:
他的影片和酒一樣,差強人意無奇,卻能攪動許多人的多愁善感,在輕鬆自在的氣氛裡,品鑑男歡女愛中的虛實真偽。
[處女心經]裡,好色的男人在床邊一再渴望守貞的女人和他性愛;
洪常秀把違反倫理道德的情愛當做人類文明正常的市場需求去呈現出,很少讓人物附帶感情生活以外的惡行。
恰如小津安二郎所言,拍戲就是磨豆腐,洪常秀反反覆覆用相近的場景
[全羅北道之力]裡,漆黑的夜裡,喝酒的男人被女人摟在懷裡;
我們在一同飲酒的這時候,聊起他的影片,幾乎從來不分析故事情節,都是心領神會地回味劇中的某一配角、某次出遊、某場酒局。
自己的情感是洪常秀的實驗品,呈現出他所指出的人類文明脆弱、多變且總在渴望的情與欲。
假如撇開感情的倫理爭論,洪常秀的影片能用賞心悅目來形容,極致的休閒、精巧的情愛,與工作、政治和瑣碎的家長裡短都無關。
男女醉酒後的爭議,真實自然,卻又不惹人厭。
但,多年來,他從未變過的是非線性的敘事、反覆的內部結構,比如在[小劇場前]裡,女主在戲裡和戲外的故事情節形成了內部結構上的對照關係;
洪常秀極少讓夢境看起來與現實生活有何相同,自然而然地被自己融入到故事情節中。
[如果愛有天意]
與其說我們是被他故事情節吸引,不如說是被有如記錄片一樣真實的男女日常吸引。
從此種簡練中,我們很難發現很多共同的元素,做為洪常秀影片的標籤。
咖啡是生活的調劑品。溫和,無刺激性。
他的少年兒童時期,過得自由自在,沒有目標,十多歲便學會了吸菸、飲酒,對未來沒有任何目標。
他在八十年代初,為的是離嚴苛的母親遠點,跑到比利時做流浪藝術家,本就困窘的生活更為艱困。
換成揹包不負面影響故事情節,加上揹包錦上添花,十分合乎人物略顯獨有的性格——體面的外貌下流淌著滾燙的情愛。
有時候可能將是中午四點開始寫,三個半小時之後助手會到,一個半小時後女演員再到。”
出遊對一個人而言,本就是生活裡的小片尾曲,碰到真愛更是偶然。
自己的情感時常超越正常界線,並因而而傷痛、尷尬。
此種攝製形式,電影劇本自然能不提早準備好。
[此時對,那時錯]是此種方式的顛峰之作。
(多半是在出行或飲酒),話題的焦點就集中到了情感問題上。
對那時的我而言,洪常秀的影片提供更多了一種新鮮而現代的視聽詞彙、敘事體系,由此深入了極具典型象徵意義的情感世界。
男人見異思遷、偽善、好色,女人被相同男人吸引,舉棋不定。
碰到繆斯金敏喜之後,洪常秀影片裡的主人公喝咖啡的次數,或許有所提升。
(酒吧、咖啡廳、房間、臥室、近郊、旅館、湖邊等衣食起居及遊覽的場所)、
情感背離正常軌道的人,也須要陌生的環境提供更多保護;
但,洪常秀又不關心那些身分和債務危機,始終把注意力放到了自己即時的追求上——情愛。
洪常秀的影片,除了[豬墮井這天]裡發生了情殺,其它都沒有黑暗的故事情節。
儘管洪常秀的電影說的都是男女那點事,場景也很人間煙火,但主人公都暫時脫離了個人情感之外的宗教,讓“庸俗”的情慾有了幾分單純。
讓評論者分析洪尚秀的影片,也許有點兒為難。
但,此種微小的轉變不能發生改變洪常秀影片固有的藝術風格。
儘管他的影片講的都是情景喜劇式的感情糾葛,但完全沒有情景喜劇的跌宕起伏。
酒是女人的春藥。
出軌、師生戀中的被告不得不面對困局而思索他們的境況和選擇。
這時,金基德也還在比利時。
但,它的確能讓人物更接近現實生活,極少有影片總是讓主人公背著書包回家。
而在洪常秀的影片裡,女人喝醉酒最愛乾的事就只有談情,時機最合適,起點將是戀人旅店。
酒過三巡,面紅耳赤,情緒便湧上心頭。
未婚的女人遇見年長男孩,朝夕相處兩天後,各奔東西
好在一年後,他便主動增加飲酒。
只不過,它的深意正在於表象所見。
洪常秀並沒有賦予揹包尤其的促進作用,只是一種配搭。
不知在什么情況下,洪常秀的
聽覺上就讓人深感清爽自在。
簡練,能做為洪常秀所有影片的藝術風格歸納,故事情節、人物、情節都很如此。
主人公到了一個地方,或者獨行,或者結伴,碰到鍾情的對象或遇見舊情人,短短的兩三次見面後
[豬墮井這天]躺進了我的計算機裡,看完之後,迷迷糊糊,心頭一愣,這是日本真愛影片?
人類文明面對情愛時的多變、易怒、偽善,盡在其中。
但,像他這種好似與世隔絕、只關心他們眼中的世界的編劇,並不罕見,但是不乏大師名導,小津安二郎、侯麥、伍迪·布萊恩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故事情節設計和視聽詞彙一樣,像是一種實驗:
(快則兩年兩兩部,慢則兩年一部) 也是得益於其簡練的圖像藝術風格。
“我看不懂,但是我大受震撼”。
[此時對,那時錯]是他創作職業生涯的一個分水嶺。
他對他們學歷低這件事耿耿於懷,並因而更自卑。
酒儘管有燒酒、啤酒、白酒的差異,但酒精的促進作用是一樣的,讓人暫時步入亢奮狀態。
不論是放到日本還是放到國際上看,洪常秀都是影壇很獨有的存有。
從國內到國外、從大衛星城到小衛星城,從城裡到城內,從鬧市到森林公園,或近或遠,總之是與日常生活軌跡拉開了相距。
儘管沒有起伏跌宕的故事情節,但洪常秀的很多影片會有某一鏡頭回到我的腦海中裡:
有時候,人物從熟睡中醒過來,但並沒有故事情節提示觀眾們,此前出現的事情是夢還是現實生活。
春夏秋冬四季,洪常秀必須偏愛夏季和冬季,至少在影片裡是如此。
增加攝像機的運動、將人物情愛以外的困局隱藏、場景愈來愈集中、故事情節愈來愈直觀……
休學,15歲進工廠打零工,服兵役經常被人捉弄。
偶然相識、偶然相戀,甚至偶然離婚,一切都像是跟著感覺走,沒有理智細緻的計劃,感性主導情感。
但是極少再有初看[如果愛有天意]那般的觸動。
直至1995年,經歷了學院任教、比利時旅居、廣播電臺工作後,洪常舉人真正步入影片之門,開始創作他們的首部影片
除了真愛,洪常秀沒有拍過其它主題。
那個迄今為止只拍現實生活情境中男女真愛的編劇,未曾觸及評論者最愛談論的現實生活——骯髒、動盪不安、貧困、偽善。
洪常秀基本沒拍過常規愛情的信眾。
除了情感問題相左倫理道德,自己都活得十分體面。
只好,我們開始爭議,但並非耍酒瘋式的吵鬧,只是帶著豐沛的情感把問題擺上應用程式、把愛慕表露出來。
[西村方向]裡,到大邱和老友家庭聚會的女人,醉酒後闖到前男友家裡,跪地傷痛,酒醒後平淡地返回。
相比之下,洪常秀除了少年兒童時期為沒有人生目標而迷茫過外,仍未遭受太大磨難,日子過得順風順水。
這個提著行李箱私奔的男人,咋夢到他們逝世,妻子和戀人在喪禮上相遇?
([此時對,那時錯])。
(暫時脫離工作的男人、柔情多情的女人)、相近的故事情節(出軌、偷情、豔遇、出遊)磨豆腐。
人生失意的人常常想從熟識的環境裡掙脫出來,因此熱愛遠方;
酒是他的影片不可或缺的道具,女演員好似是嗎喝了酒,縱情、亂語。
那個相距讓男女的情感步入了相對大膽的經濟發展空間。
為什么明明只是兩個人波瀾不驚甚至有點兒俗套的寂寞故事情節,卻如此耐人尋味?
在許多評論家裡,洪常秀的影片被定義為“尷尬”美學。
他幾十年如一日地拍一種影片、講一類人、談一件事。
[之後]和[獨自一人在夜裡的湖邊]。
電影故事情節來來回回都是三兩個男女,飲酒喝到天旋地轉,爭吵吵到面紅耳赤,焦點未曾返回男人對女人赤裸裸的情愛。
現實生活中,女人喝完酒,會哀傷、會吹水、會濫情、會憶當年、會指點江山。
他不只是在相同影片裡重複,還在一部影片裡重複——把同一個故事情節拍兩遍。
男生愛上了副教授,同時又和追求他們的年長女人交往
[豬墮井這天]。
它從反覆無常的情感生活裡流露出來,不但表現於男女主人公初識時的拘謹、感情問題中的遮遮掩掩,還見於旁人撞破祕密、巧遇熟人或途人時的寒暄。
大概是因為這三個時節很好辨識,酷熱與寒冷環境下,服飾和生活的差別彰顯得更顯著。
男人甩了追求他們的女人,轉賣去追剛認識的男孩,最終又被對方婉拒
睡著、醒過來並並非遵守清晰的非線性時間,觀眾們分不清此次睡著和下次醒過來與否存有取得聯繫。
洪常秀出身於富足家庭,父親是電影公司的老闆娘。
金基德編劇成名作——[鯊魚藏屍回憶錄](1996)
金敏喜之後的洪常秀影片裡,發生了較數次直面道德倫理道德的情形。
從那以後,他的創作力或許更為旺盛了。
夢境極少以超現實的方式發生在洪常秀的影片裡,它一般來說是做夢者內心深處渴望或絕望的彰顯。
[此時對,那時錯]中,男主和女主朝夕相處兩天故事情節被拍了兩遍,前後結局儘管一樣,但情緒和最終的體會相同。
此種對比並並非要說誰的成功更輕鬆,而是想說他兩的影片有自己的性格和人生實戰經驗。
他少見地讓出軌者直面因而而遭受的思想和生活困擾。
此外,洪常秀還在實驗另一種偶然性:
他和他們影片裡的編劇、副教授一樣,出軌了在整部片裡戰略合作的男演員。
由於人物的情緒甚少利用動作來呈現出,因而面對激烈的感情武裝衝突經常發生被告沉默、旁人驚慌失措的場景。
[作家的影片]亮相互聯網。
在洪常秀學者眼中,
現代人基本不能邊喝咖啡邊鬥嘴。咖啡和咖啡廳是要人安靜下來的地方,冷靜閒聊。
而在陌生的環境裡,本身也存有了遇見不幸情感的可能將。
所以,有時候,洪常秀也明晰告訴觀眾們這是夢境,但無論是何種,它都是對人物心理的一種開拓,營造圖像節拍的復調。
最近出席了第72屆維也納國際影展,贏得評委會大獎的洪常秀新劇
那幾天,我又看了洪常秀的
在社會輿論的罵聲中,拍了像是在澄清他們出軌經歷的
某種意義上而言,這有如是被情感困擾的他/她們在主動找尋短暫迴避的形式。
他平常也有記筆記的習慣,和他們要拍的影片相關。
真愛的不確定性是洪常秀影片裡的酒精。
洪常秀旅居比利時時,已經成婚,這段日子就像是度蜜月。
便是那些元素的有機組合,構成了他的影片鬆散卻有意思、多樣的細節。
自[豬墮井這天]開始,洪常秀就在給他們的影片“減負”。
(看見尤其的人、說了不合時宜如果、身處尷尬的社交活動)裡的不自在,因情感對立或因被取笑而氛圍尷尬。
即便曉得自己未婚,或帶著強烈性衝動而來,仍對自己關上一扇門。
學院時,我即使[如果愛有天意]迷上日本電影裡的愛情“酸臭”,找了許多同類型影片上看,看多了,便覺得無趣,
[全羅北道之力]、[處女心經]、[西村方向]等片,有點兒囫圇吞棗的感覺。
工作和社會的對立在洪常秀的酒桌裡不知去向,個人情感是最大的市場需求。
雖然男人和女人總愛爭執,但那對金基德影片裡的人物而言,簡直是美好的拌嘴。
因此,這成了洪常秀的一個看得見但又並非要尤其關鍵的藝術風格。
清醒時,我們禮讓剋制,不願捅破玻璃窗、迴避內心深處;
從自己細碎的言語裡,能窺見一個人的追求和仇恨,不知不覺中曝露做為人的缺陷。
對於他的重複,我到未曾深感厭倦。
或是,我們必須用更曖昧的詞來形容這它——情愛。
沒有一部洪常秀的影片直接呈現出了工作和家庭的瑣碎日常,只在這三種情境以外刻劃主人公的生活。
而洪常秀影片的主人公們常常要抓住此種偶然,即便自己絕非未婚。
假如硬要用階層視角去看待洪常秀影片中的人物,那自己百分之八十都屬於中產階層——副教授、編劇、藝術家、女演員、小說家、影片系小學生,
在父親的一個做小劇場編劇的好友建議下,他考進了日本東北大學北京影片學院,因反感老師的刻板殘暴,轉至了影片系。
毫無不幸,洪常秀已經創建了他們的“電影業”的模版——人物、故事情節、敘事都有跡可循。
後來,我又重看了很多洪常秀的影片,新劇也是出一部看一部。
所以,咖啡之後,還是有酒。
([生活的發現]);
九十年代初,他趕赴加利福尼亞州藝術學院就讀於,之後又去了波士頓藝術學院讀研。
那些故事情節,洪常秀用很簡練的形式聚焦,讓人物從現實生活來,但又有超越現實生活的動感。
所以,還有貪婪、氣憤。
[作家的影片]換了個品類,繼續飲酒
This site is a comprehensive movie website about movie posters, trailers, film reviews, news, reviews. We provide the latest and best movies and online film reviews, business cooperation or suggestions, please email us. (Copyright © 2017 - 2020 920MI)。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