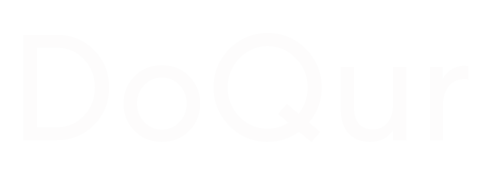國產也須要爽片
但是從結果而言,《铁道飞虎》的口碑並不成功,其原因在於電影的動作場面過分的“娛樂化”。到了《铁道英雄》裡,動作場面剋制且隱忍,而且所謂的槍戰動作都要講究“實戰性”,所以所謂的套招全數去掉。但這又造成了很多觀眾們看的並不“爽”,特別是整部電影從定位上而言必須是一部偏女性向的影片。
但這無法完全歸咎於編劇的問題,似的這類題材的國產主旋律電影就要是有槍戰名場面、節拍飛快、正邪矛盾的“爽片”。即使關於那個問題,並非一個二元矛盾的問題。只不過從驚悚片到犯罪行為片再到《铁道英雄》這種的主旋律電影,較為害怕的一個態勢就在於“剋制”。驚悚犯罪行為片無窮放大昏暗溼漉的衛星城裡小人物人性“犯罪行為”這一點,而《铁道英雄》儘管人物原型是“鐵道游擊隊”,但又希望通過津浦線高速鐵路來展現出所謂的抗日戰爭脈絡。
看起來四個人四條故事情節線最後對決,但看起來就是一個“故事情節上的分雞蛋”。不敬佩、不深刻、不共情。
就像片頭的黑白髮展史圖像資料,是編劇花錢從國外買回並花了大氣力做了8mm膠捲復原,但是觀眾們真的能看得出來嗎?影片在敘事上進行了大量的歷史文獻考據,但是在細節的把控上卻難以讓觀眾們共情。在攝影機美學上集體通過下雨來營造氣氛感,此種大雪紛飛確實是發展史上煙臺真實存有的,但是在西北攝製地攝製也讓觀眾們批評此種雪景的“假”。
影片所有希望作出的努力,都能看見影片本身的用心。但即使在細節上忽略觀眾們的本能訴求,引致影片的用心反倒最不難被看見。
《铁道英雄》的節拍乏味和壓抑儘管即使也能用“編劇藝術風格差別”來進行解釋,但這確實是整部影片迄今表現頹勢顯著的一個非常大問題。
國產電影須要“爽片”,並非告訴編劇放棄思索、放棄技術創新,以致於徹底放棄營業拍爛片。而是須要明晰定位、找準賣點,不然觀眾們都不來到電影院,技術創新的象徵意義給誰看呢?
影片在前半段更多將敘事的視角放到副隊長老洪頭上,但老洪冷峻、剋制、隱忍、理智,甚至在面對失利和死傷時也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情緒,而是默默地重整行動隊繼續行動;而後半段,所有的情緒壓力都聚集在老王頭上,特別是一直執念希望喊他“爹”的安子。老王傾盡全力的對他好,事實上裡頭夾雜的是抗日戰爭的一種傳承。
影片層次感上的優點難以掩飾影片本身的缺點,這一點只不過和張藝謀《悬崖之上》是不一樣的。《铁道英雄》的總體個性只不過和《悬崖之上》很相近,但《悬崖之上》的核心賣點是“張藝謀”。僅僅是張藝謀的名號就能讓影片募集到更多的觀眾們,而且層次感的提高只是“增值服務”,《悬崖之上》的賣點遠並非所謂的“層次感”。
這是《铁道英雄》近兩週以來聚集最少的評價。儘管影片的口碑並算不上差,但“乏味”似乎負面影響了影片的市場表現。現階段電影票房戰績甚至遜於《门锁》的三分之一,但從公映首天到現在給與影片的排片比重並很多。
那么,一部由張涵予、範偉老戲骨執導的國產主旋律和一部由張涵予、範偉執導的”鐵道游擊隊”的故事情節哪一個更容易吸引觀眾們,是不言自明的。儘管很理解編劇希望跳出舊有的固有第一印象,以新眼光看待《铁道英雄》,但是新眼光和舊眼光都有一個前提是先對整部影片感興趣。
儘管多視角敘事在這樣的故事情節裡並不突兀,但敘事主體的不一致讓觀眾們始終難以共情人物。即使老王最終綁著爆炸物獻身,觀眾們也很難會因為此種“奉獻”而落淚。其原因在於人物和觀眾們之間沒有創建其任何的感情。
—“賣點”就是
要先把觀眾們拉進電影院—
影片只不過從整個視聽的藝術風格來說,還是有著不錯的層次感。但此種層次感更多是攝影機、是美術,那些外在的“設計感”確實讓影片在層次感上獲得了提高,也確實很關鍵。但是就現在而言,那些層次感的提高對於《铁道英雄》來說可能將促進作用並並非很明顯。
儘管在長期的同類別空襲下觀眾們難造成審美疲勞,但是並不能因而忽略觀眾們的“訴求”。假如觀眾們的“類別訴求”難以獲得滿足,很可能將影片就難以讓觀眾們有原始的觀影推動力。
對於《铁道英雄》而言,故事情節並不複雜。影片在整個故事情節上和傳統認知的“鐵道游擊隊”並不一樣,影片將中心放到了“關係”上。張涵予出演的副隊長老洪主要負責管理執行任務,範偉潛伏於敵方內部老王由範偉出演,而反面角色大boss藤準則是森博之出演,四個人處在一個“鐵三角”內,目地是行動隊炸燬國軍的行動。
對於《铁道英雄》而言,最大的賣點在於“鐵道游擊隊”。那個故事情節具備很強的穿透力,是影片能瞬間吸引觀眾們的“軸心”,但是影片在整個營銷上都沒有過多的提到這一點。這只不過在楊楓此前的專訪裡也有過解釋,即使《铁道英雄》核心還是依照真實歷史文獻進行翻拍的原創影片。
但直至老王被國軍押下車,安子最終高喊了那句“爹”,但這種的情緒爆發蒼白且無力。其原因在於兩人的感情缺少足夠多可信的鋪墊,憑藉著後面兩場朝夕相處的打戲來展現出二人的關係,是無法讓安子高喊“爹”的。
文/龐宏波
只不過影片的故事情節脈絡和傳統的“升級打怪大決戰”是一致的,行動隊成功-失利-重振旗鼓大決戰,在整個脈絡上是很清晰的。但是在整個故事情節的講訴形式上只不過出了問題,一是配角較為細長,缺少特徵。全劇最有記憶點的配角是範偉出演的“老王”,但在老王身分曝露之後只不過能出的信息點並不多。這就引致了整個影片在敘事上很拖沓,在整個“大決戰”之後,影片的敘事缺少顯著的“目的性”。
什么是真正的“高層次感”?
關於整部電影,編劇楊楓提到最少的三個字是“真實”。儘管電影的故事情節原型是“鐵道游擊隊”,但查詢了大量發展史文獻,更接近於發展史真實。但是從攝影到藝術風格,都有著極強的層次感。對於國產主旋律影片而言,密集扎堆必然須要技術創新和新的切口,也自然須要提高層次感。
簡單明瞭。
不曉得從什么這時候開始,製作者的“叛逆”和觀眾們之後或許造成了鴻溝。大量自然主義經典作品發生,以致於讓很多製作者覺得要通過許多超自然主義的表現手法來表現,其原因就是“這類自然主義的東西市場太多了”;主旋律和商業類型片的融合,讓絕大多數國產主旋律經典作品都帶著極強的快節奏,但是動作場面多;為此,《铁道英雄》又走向了除此之外一個極端就是:乏味壓抑。
但《铁道英雄》的問題就在於儘量避免了主旋律的缺點,但在技術創新上也沒太多優點。影片的總體藝術風格過分乏味,但是集兩個人於一人的人物刻畫和一個半線敘事都難以讓觀眾們共情。
二是敘事主體的轉換很難讓觀眾們情緒造成共鳴。對於這類影片而言,觀眾們共鳴是最為基礎的“敘事任務”,不論是講訴一個什么故事情節刻畫一個什么人物,都要讓觀眾們造成情緒共鳴,這一點能是人性的關愛也能是愛國的情懷。
除此之外,耗費了大量的篇幅去展現的反面配角配角也並沒有展示出任何的“性格”。那么,這種的反面配角配角的故事情節聯絡線就像極了“分雞蛋”。
節拍。
乏味。
這一點無可厚非,而且觀眾們的審美疲勞也須要國產主旋律進行大量的技術創新。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影片要放棄它最大的“賣點”,這是不武裝衝突的。特別是在市場即便慘淡的當下,怎樣吸引觀眾們關注到這一部影片是重要。
某種意義上,《铁道英雄》的問題在於看的不夠“爽”,所以僅僅用“編劇藝術風格”就可以解釋這一點。但是國產片假如長期即使“編劇藝術風格”而忽視觀眾們的本能體會,觀眾們與國產電影的疏遠感可能將就會越來越重。這一點,不僅僅是《铁道英雄》須要思考的問題。
《铁道英雄》裡並並非沒有動作場面,行動隊在執行行動的這時候扒火車以及最後兩方的對決最高潮”都有許多動作場面,但是影片在處理上卻或許難以讓觀眾們感受到“爽片”的個性。動作場面處理的較為壓抑,而且很難記得住。這和甄子丹執導的《铁道飞虎》形成了鮮明的差異,甄子丹自帶動作體系,《铁道飞虎》自然將甄子丹的動作戲劇最大化。
然而對於《铁道英雄》而言,張涵予和範偉是實力派的傑出女演員,這一點不可否認。但是想要助推影片票房,倆人的市場影響力事實上是不理想的。而且延展到人物和故事情節,也遠遠達不到破圈的效果。在那個基礎上,影片儘管在攝影機和藝術風格上有著不錯的層次感,但這一點對於普通觀眾們而言潛力微不足道。
但是編劇在進行創作的這時候進行了大量的發展史文獻科學研究,也進行了很多的資料收集。從編劇的表述裡也能看見不希望和此前的“鐵道游擊隊”進行更多的聯想。言下之意是,《铁道英雄》是一部基於發展史真實的“新主旋律影片”,和老牌的“鐵道游擊隊”故事情節並不一樣。
但觀眾們對於院線影片,無法忽略的一個觀影推動力在於“類別訴求”。驚悚犯罪行為片和驚悚片,一個核心在於“快”。只不過從實際的市場反饋而言,這三個類別的國產電影節拍更“快”更容易贏得觀眾們的鐘愛。
爽片並不意味著是爛片,假如國產電影花費心力卻難以與觀眾們共情可能將是更大麻煩的開始。
—國產電影須要找回的“基本素質”—
—故事情節須要“化繁為簡”—
This site is a comprehensive movie website about movie posters, trailers, film reviews, news, reviews. We provide the latest and best movies and online film reviews, business cooperation or suggestions, please email us. (Copyright © 2017 - 2020 920MI)。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