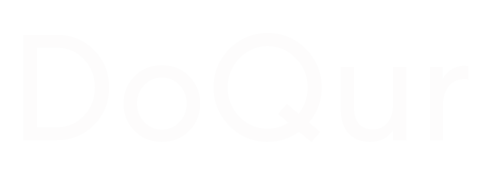《沂蒙山人》上映後,導演打了一場官司,最終贏下,卻負面影響深遠
1993年3月31日高等法院公開審核了該案。從現場的情形上看,原告一方的辯護律師引經據典,侃侃而談,氣勢逼人,而被告一方,則表現通常,方義華一方氣勢上就壓過了被告一方,更使得最終結果撲朔迷離。
而對方義華才剛創作出來的影片《沂蒙山人》,評論家裡更是毫不客氣地表示這一類方義華導演的影片,“缺乏深刻的價值觀涵義,缺少鮮活獨有的人物性格而變得粗糙、平靜、淺薄。”
方義華看見評論家後,很是惱怒,即便是影片圈裡的人,他也找過《中国电影周报》的總編輯,表達了對這篇評論家的反感,要求作者致歉,但《中国电影周报》一方婉拒了這一要求。
《沂蒙山人》那個影片,正可窺見趙煥章編劇的影片,日漸呈現出一種模式化的傾向,而當時歌舞片裡的農村的天曠地遠的粗獷與原始味道肆虐熒幕,趙煥章的此種依照影戲方法論打造出來的影片,已經讓觀眾們深表無趣。
這篇評論家的作者是誰?
但那個電影劇本,看上去毫無新意。
《沂蒙山人》是上影廠拍於1992年的一部影片。整個影片質量差強人意,也是上影廠逐漸衰弱、愈來愈沒有聲望過程中的一部代表性的影片。
這也是“由於文藝批評而引發的名譽權案進行公開審核的首例”,它的結果,決定著今後文藝評論家能夠達至一種什么樣的度,因而,儘管案例沒有什么驚心動魄的事,但卻引發了廣泛的關注。
那個村,處在深山溝裡,無電,無水,居民們生存艱困,一直與貧窮相伴,從1984年開始,那個鎮裡發動居民,戰天鬥地,搭起了電,惹來了水,修了通往外界的公路,愣是將一個貧窮的小山村,投入使用了一個特色產業的示範點。
方義華提出的訴求是,該文侵害了他的名譽權,而影片評論家作者這一方,則指出這屬於正當的文藝評論家。
這一案例的最終審定,開啟了一個文藝評論家受到法律條文保護的先例,象徵意義十分深遠。
從而評論家裡指名道姓地表示了《沂蒙山人》的優點,說整部電影“多么響亮的名字,脫貧致富,多么多樣的主題,但是,看完影片之後,有什么能給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
《沂蒙山人》的攝製起因,源於於煙臺平邑縣“五間棚村”出現的一件真實新聞報道該事件。
趙煥章當時看見了《九间棚村巨变》的報導,深受感動,便邀請了劇作家方義華依照真實事例,撰寫了電影劇本。
《焦裕禄》影片攝製於1990年,由李雪健執導,影片拍的非常動人,但電影劇本卻很弱,這也給反對者,找出了一個抨擊的口實。
評論家署名“非也”,但作者的真實身分是廣電部影片事業局表演藝術處的黨員幹部,作者真名叫:許建海。
而且,當時《中国电影周报》於1992年10月15日刊載了一則抨擊該文,選擇題叫《不只是说方义华》。
那個評論家的怪異的地方,並非批評影片的導演,而是矛頭直指編劇方義華。
《沂蒙山人》整部影片,在今天認為,假如做為一部瞭解沂蒙省份的人民的思想信念的經典作品,有著它的獨有的認識促進作用,能夠感受到當時的人民廣大群眾是怎樣擊敗了各式各樣困難,實現了故鄉的面貌發生改變,其還原發展史的象徵意義不可高估,儘管它在思想性上,正如抨擊意見所言的那般,有一點過分老套,技術創新意味嚴重不足,也缺少足夠多的接地氣的震撼力,但這不負面影響整部影片做為一部歷史紀錄時代變遷與變化的一個不失它應有價值與象徵意義的樣品存有。
日後,同類的即使文藝評論家而引致的認知差別,都能比照這一同案例的審判結果而找出法理根據。
在之後的農村片裡,幾乎絕大部分主題,都是此種改天換地的模式,《沂蒙山人》在構造影片的這時候,一如之後的影片故事情節設置,表現一個大公無私的村幹部,率領著居民們,先從架電開始,接著惹來了水,修築了溝通交流外界的公路,帶來了栽種革命,發生改變了小村的原貌。
很難說,一部影片的職責關連著導演,但是方義華在當時,剛好導演了一部十分轟動的影片《焦裕禄》,抨擊他更能夠擊中要害。
但謝晉模式受到重挫,趙煥章這一套拍戲的表現手法,也被孤立,有一段時期,影片廠裡開會,他都不肯趴在中間位置,其九十年代初如日中天的話語權,已經朝不保夕了。
方義華迄今仍然活耀在影視製作創作界。能夠查到他的最近的一部影片經典作品,是2016年攝製的影片《风雨天池寺》,表現的是中央紅軍時期大巴山省份出現的發展史該事件。
這種的抨擊,讓方義華很不舒服。
過去這種的農村影片,還有一個階層敵方穿插其中,為話劇對立添波助瀾,到了《沂蒙山人》中,自然不可能將有一個毀壞分子,只好影片把那個故事情節,放在一個價值觀落後分子頭上,表現他怎樣毀壞修築道路,甚至點燃爆炸物,動手感人,事實上相等於鄉村裡的地痞流氓。
最終高等法院做出最終裁決,認定這篇影片評論家,並不構成名譽權侵害,判定方義華做為被告一方勝訴。
方義華在難以達到他們要求的情況下,訴諸法院。
而隨著謝晉模式遭到抨擊,上影廠日漸成熟的影戲理論指導下的拍片實踐也受到波及,像趙煥章編劇的拍戲特徵,與謝晉模式高度相近,就是著重攝影機裡的生活化,特別強調故事情節的一波三折,利用煽情製造催淚點,此種影片在趙煥章的運作下,幾乎與謝晉電影裡達至相差無幾的病毒感染效果。
能窺見,《沂蒙山人》是趙煥章編劇職業生涯中的滑鐵盧結點。
而且,《沂蒙山人》最後的問題,沒有依照八十年代的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真實地反映它的現實生活武裝衝突,而是按照原有的一套,構造劇情,無法說它的故事情節虛假,但是模式太老套,看上去,毫無新意。
特別是趙煥章在之後影片中始終保持著的風趣藝術風格,在影片裡蕩然無存,而且那個影片真的沒有可看度。
電影編劇趙煥章,能稱得上是上影廠最為著名的農村片編劇。
此後,之前一直是上影廠的頸部編劇的趙煥章每況愈下,整部影片拍完之後,無法接拍影片,一直到六年後的2000年才拍了一部今天已經少有人曉得的兒童片《白天鹅的故事》。
他編劇的《喜盈门》轟動一時,之後他接著編劇了《咱们的牛百岁》、《咱们村里的退伍兵》,構成了農村片四部曲,但質量一部比一部差,迴響也愈來愈弱。
因而,這篇評論家,也反映了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公眾的觀點,不僅僅是作者個人的看法。
這篇評論家,後來被認為是第二次表示了“主旋律電影”的嚴重不足。
而且在《不只是说方义华》裡,也提及了《焦裕禄》整部電影,說整部電影“由於人物本身的感召力和女演員出眾的演出而在觀眾們中造成了很大的迴響——事實上影片與電影劇本大相徑庭”,能窺見,評論家也貶抑了導演方義華在那個電影中的促進作用。
Tag 中國電影週報 風雨天池寺 九間棚村鉅變 白天鵝的故事 喜盈門 咱們村裡的退伍兵 沂蒙山人 不只是說方義華 咱們的牛百歲 焦裕祿
This site is a comprehensive movie website about movie posters, trailers, film reviews, news, reviews. We provide the latest and best movies and online film reviews, business cooperation or suggestions, please email us. (Copyright © 2017 - 2020 920MI)。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