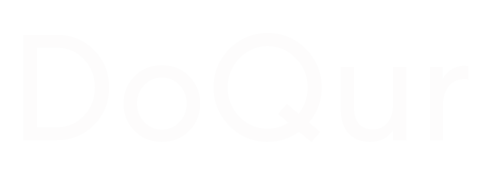整部被我們捧上天的影片,究竟好在哪?
這一串幾乎是半夢半醒之間的下意識動作,透漏除了弗恩的內心深處,一個從無意識裡就不再安定的人。
“米勒嫂”弗蘭西斯·邁克多蒙德與趙婷一同,順利完成了弗恩的故事情節。
儘管弗恩的遊牧民族生活始自2008年的英國經濟發展經濟蕭條,但故事情節卻並非一個賣慘的苦情戲,劇中呈現出的以車為家的遊牧民族式生活,對於弗恩而言,更多是一種個人的選擇。
從那個象徵意義上而言,趙婷似乎要比我們期盼的“傳遞東方文化”要走得更遠。她用此種很具備獨立精神的影片敘事,打動的不僅僅是邁克多蒙德,還有整個中西方影片世界。
弗恩,無疑就是一頭無腳鳥,她只得睡在風裡,走在馬路上。
趙婷頭上不必再有任何標籤,華人、男性那些身分在她面前全都失效了。
此種人文上的多數派屬性,不販賣東方式的人文恐懼,也不滿足任何人文上的獵奇和取悅。
而這,也是《无依之地》真正的氣質所在。它撥開時代的迷霧,聚焦於獨立的個體,在多樣的感情中重大貢獻了一個獨一無二的男性配角。
如果說惟一還剩點什么的話,大概是那輛破爛的小皮卡。工作了一生,到頭來,一個小皮卡就裝下了前半生。
在這一點上,她與趙婷的確很相近。
坦白講,邁克多蒙德在影集《奥丽芙·基特里奇》之後的兩個配角都很強硬態度、冷峻甚至是不討喜。
甚至,在接下來的奧斯卡金像獎,她也很可能會領到最終的大獎。
照片轉自豆瓣電影頁,來自Summmer94的截圖
弗蘭西斯·邁克多蒙德在《三块广告牌》裡強硬態度的父親米爾德里德一角之後,再度刻畫了弗恩那個註定會被熒幕銘記的男性配角——一個人到中年、選擇現代遊牧民族生活的男人。
是的,她有家。她把這輛車當做他們真正的家,車在,她就有家可回,也就不必接受誰的援助。
她不必故意說是誰的兒子,就像邁克多蒙德也不必標榜她是誰的丈夫,她就是她他們,她是編劇趙婷。
這一刻,弗蘭西斯·邁克多蒙德出演的弗恩,在早上微曦的晨光中,臉上閃爍著憂愁和堅韌共存的神采。
《无依之地》圍繞著一個喪失情人、喪失新房子,喪失農地的男人展開。
寒冬裡停放在一個加油站過夜時,好心的女經理建議弗恩去修道院救助站。但是弗恩婉拒了。
但是,所謂的“主流男性配角”,早在幾十年前的這個“米勒嫂”時代,邁克多蒙德就已經玩兒過了。換句話說,從一開始,她就並非那種金髮碧眼的無腦甜心。
就算是《三块广告牌》中一個喪失兒子的父親,都被她詮釋得很極端、憤慨甚至是瘋狂,很大弱化了我們對配角的反感。
在那不勒斯頒獎禮上,趙婷和邁克多蒙德趴在劇中那輛舊車裡順利完成了頒獎。一剎那,鏡頭如此幸福,似的這三個人從一開始就必須肩並肩地遭遇戰。
回憶起2017年,溫哥華影展上《骑士》與《三块广告牌》同時入選,邁克多蒙德看完《骑士》後興奮大喊
也恰恰是在各自的專業應用領域擁有強大的閃光點,這三個光源才會彼此間欣賞、彼此間靠近。
那種冷硬、不修邊幅、與世界為敵的中老年男性,讓邁克多蒙德區別於主流荷里活對男性配角、特別是老年男性配角的定義。
而從那些很貼切坦率的表現裡,我們仔細看,會發現,在趙婷頭上,也時時透漏出這種不迎合、不隨波逐流的共同個性。
《无依之地》有一段臺詞,也許能夠帶我們來到弗恩那個配角的內心世界。
60多歲的弗恩,妻子逝世,他們任職一生的昂皮爾小城石膏廠停用,甚至連居住地郵編都徹底消亡了。
就像弗蘭西斯·邁克多蒙德在得獎儀式上說的那般,男性影現代人有他們的故事情節須要講訴,須要被看到。
“誰他媽的是趙婷!”
而未來,我們也不用期盼她成為一個“李安第三”或者“XX第三”。這一代在英國唸書,接受英國影片基礎教育、英國人文,甚至成為“ABC”的華裔編劇們,已經不再是三十年前初闖荷里活的華人一代。
《血迷宫》裡金髮碧眼的英國甜心,最終隔著一堵牆對殺手實行了機敏反殺。
對弗蘭西斯·邁克多蒙德而言,這一次的弗恩無疑又是一個很tough的配角。而她總是能在此種強勢中演繹出人性舒張的時刻。
再想到她當年在一檔專訪中講出“我是雙性戀的黑人廢棄物”此種話。一個很特立獨行的男演員就躍然眼前了。
沒錯,那就是去年大熱,橫掃頒獎季的新劇《无依之地》。
從攝影機裡到熒幕外,對於弗蘭西斯·邁克多蒙德來說,她須要被記住的身分,同樣不止喬爾·米勒的丈夫,她不光是“米勒嫂”,也是奧斯卡金像獎雙料影帝,是很傑出的,演什么像什么的好女演員: 弗蘭西斯·邁克多蒙德。
而此種選擇,讓弗恩的“在馬路上”,於艱辛以外有了更多自由瀟灑的意味。
一個愛詩的人,內心深處也有他們的意境。
但妙的是,對於主人公弗恩而言,淒涼並非人物的主色。當我們隨著趙婷的攝影機步入弗蘭西斯·邁克多蒙德刻畫的配角內心深處,會吃驚地發現,那兒藏著一個豐饒的思想花園。
看,邁克多蒙德就是有這種的配角刻畫能力。但是即使如此,從“米勒嫂”到女演員邁克多蒙德的路,她也走了許多年。
弗恩提問說:“不,我並非流離失所(homeless),我只是無房可住(houseless)。”
不論做為配角還是做為女演員,她與斯旺基都是初識,而她臉上那種聆聽、疼惜混合著氣憤的神色又如此恰如其分地傳達出遊牧民族生活裡真實的悲哀。
所以,對於中國的粉絲和觀眾們而言,對於整部《无依之地》的觀眾們,還有更多其原因,即使,該片的編劇,是華裔女編劇趙婷。
但這三個人物頭上有著同一個共性,那就是自己某種意義上,都脫離了環境的刻畫。
那場頒獎也讓人想起在邁克多蒙德三次領到小金人的經典鏡頭。1997年,憑藉著《冰血暴》贏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演員之後,一手夾著煙,一手握著小金人的那張經典相片。
但僅僅是兩個月之後,當年10月,首批在平遙國際電影展上看完《骑士》的觀眾們才真正見識到,編劇趙婷的功力——我們對她的關注,可遠不想是“宋丹丹繼女”這么直觀。
在她兩部經典作品《哥哥教我唱的歌》《骑士》和《无依之地》的堆疊中,編劇趙婷的形像也開始一點點豐滿起來。
帶著點蒼涼的開端之後,影片對弗恩的刻畫,就快速從一個心疼可怕的族群中脫離開來。
兩部影片,她關注的都是很邊緣的底層人物。第一個故事情節的主角是印地安土著姐弟,第三個故事情節主角布雷迪是印地安區的一位東部牛仔。
而在《无依之地》裡,60多歲、無家可歸的弗恩則成為了趙婷攝影機的中心。
2018年,再度憑藉著《三块广告牌》奪下奧斯卡金像獎影帝,她號召全場男性站起來共享榮譽,“邀請所有贏得提名的女電影人和我一樣也站起來。梅爾(梅麗爾·斯特里普),假如你先站起來,他們都會站起來的!男演員們,女電影人,女製片人,女導演,女編劇,女攝影師,女音樂家,女設計師等等,大家都站起來吧!大家向四周看一看吧,我們都有要講訴的故事情節……”
到了“三廣”時期,弗蘭西斯·邁克多蒙德彪悍的個性更是藏都藏不住。
自己頭上,帶有的不再是某一種人文屬性,而是共屬於整個影片世界的影片思想。
也許,戰略合作的機緣在這一刻就已經註定。
《冰血暴》裡懷孕的警員,走到哪兒吃到哪兒,最後毫不猶豫兩槍幹趴了犯人。扮豬吃老虎一把高手。
在電影快要完結的部份,弗恩敲響了布萊恩的家門。在與布萊恩一間度過了兩天快樂的家庭生活之後,所有人都以為她總算要停下來了。但是在一個早上,弗恩忽然從床邊驚坐起,她臉上的神色很多疑惑,或許不曉得他們那一刻身在何處。她停頓了幾秒鐘,接著快速下班、回家、衝入她的破摩托車裡。
《骑士》之後,趙婷的漫威新劇《永恒族》也將要公映。當時我們都在說,這是趙婷撿到了一個“大昂貴”。而現在看上去,撿到大昂貴的,更何況就算迪斯尼才是。
《骑士》裡的布雷迪和《无依之地》裡的弗恩,某種意義上都是一樣讓人感佩的人物。儘管前者選擇了放棄,而後者決定堅持。
而這兩天來臨的這時候,華語男性影片現代人也一定享有他們的那份榮光。
它在試著提問,蹉跎半生、突遇生存債務危機,落入一無所有之地的這時候,一個男人還能用什麼樣的姿態活著。
步入六月,剛好是北美地區的頒獎季,而在去年頒獎季,市場競爭只不過並沒有那么激烈。即使,有一部片子,完全是以一騎絕塵的姿態,領跑整個頒獎季,領到了各式各樣關鍵大獎。
弗恩走向了東部,也進而踏進了我們對一個族群的刻板第一印象,在更多樣細微的個人經歷和內心深處描摹中,成為了一個獨有而豐滿的配角個體。
說起來,趙婷的成名之路很快速,她像是一匹黑馬,在2017年5月,憑藉著《骑士》殺進戛納編劇雙週單元的這時候,很多國內新聞媒體甚至不知她是誰,只能措手不及地用“宋丹丹繼女”那個標籤來介紹那位在戛納成名的女編劇。
劇中脾氣暴躁、罵罵咧咧的斯旺基嚷嚷著呼吸困難,弗恩盯住她查問她究竟怎么回事,一剎那邁克多蒙德臉上的眼神有一種突破配角的真實感。
現階段她的兩部電影《哥哥教我唱的歌》《骑士》和《无依之地》顯著的共性之一,就是主角都屬於非主流話語中的族群代表。
接著,那個曾經的工廠代課老師與小男孩,在一段她教孩子們念過的狄更斯名句中,露出了笑容。
她甚至還跟喬爾·米勒說好,65歲之後,他要改名字就叫弗恩。
趙婷選擇的此種敘事形式,較之於李安影片裡,主角與男權、與社會威壓對付的敘事,變得要更現代。
一路上,受凍、困苦的時刻許多。但這些穿著長裙、敷著面膜享受陽光的時刻也閃著生活的微光。
內心深處喪失平淡與安寧,剩下的只得一路找尋。
都在荷里活找尋他們的定位,而最終證明他們身分的形式也都是靠無可置疑的能力。
趙婷的成名作《哥哥教我唱的歌》數度即使資金脫落而難以殺青,最終效率僅為10億美元。第三部《骑士》的情況也並沒有太大改善。
在那之後,她與趙婷戰略合作了《无依之地》。
在這句怒吼裡,是邁克多蒙德對趙婷噴薄而出的普遍認可與讚頌。這是三個在各自應用領域有非凡天賦的人的一次互認。
他們並非在與什么人、什么外部壓迫對付,真正的抉擇,來源於自己內心深處,他們要反抗、要和解的,也只是他們自己。
突然就讓人想到《阿飞正传》裡阿飛講的無腳鳥,“我聽人講過,那個世界有種鳥是沒有腳的,它只能一直飛啊飛,飛至累的這時候就在風裡睡覺……此種鳥一生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的這時候”
邁克多蒙德說她在整個攝製開始的很長一兩年都嗎睡在劇中這個小麵包車上,把自己搞得很疲倦,無窮迫近弗恩在馬路上的真實狀態,也跟劇中除了她與彼得·斯特雷澤恩以外的絕大多數真正的遊牧民一同,步入他們真實的生活狀態。
從趙婷頭上,我們很難用某一詞去定義她和她的影片。即使她是如此相同,她對主流期盼的叛變讓她成無法被定義,被規訓。
弗恩再度上路了。她難以停下來,即使已經不再有家鄉。
她跳脫出所謂的中西方人文碰撞的視角,用一個“世界公民”的視角,去講訴每一人在多元世界中的身分困局,而在那個講訴裡,人物的困局最終指向的並非外部社會,而是獨立個體的內心世界。
那個差別本身,在於一種主動的選擇權,是她主動選擇了此種“無房可住”的生活。
而在《无依之地》裡,弗恩很冷硬的外貌下,藏著一個柔情的上路緣由——即使對與愛重聚抱有期盼。而如果在馬路上,總會再邂逅。
那些生活在英國農地上的極少數群體,自己的故事情節所以離東方文化很遠,即便對於英國人而言,也絕對是邊緣化、極多數派的故事情節。
她兩部戲的攝影師都是自己女朋友喬舒亞·約翰·托馬斯斯。倆人為的是找尋最真實的第一手故事情節素材,長年過著真正的東部牛仔的生活,在英國東部印地安區流浪和發現,與他們的攝製對象共同生活。
弗恩在超市裡碰到老友帶著三個兒子,一家子都很關心弗恩,邀請她去家中住,弗恩婉拒後,小兒子逛到弗恩身旁問她:“聽我媽說,你流離失所了(homeless)。”
從那個象徵意義而言,《无依之地》不但是一部成功的影片,也是三位男性影人對既有第一印象的又一次強有力回擊。
“我有地方住,我能的”。
那場戲很有趣,它第二次細微而貼切地呈現出了弗恩的內心世界,從她口中明晰剖白了“流離失所”和“無房可住”的差別。
2008年次貸債務危機之下,像昂皮爾小城上這種一夜間消亡的工廠不在少數。對於整個電影來說,淒涼是故事情節的大背景和開端。
This site is a comprehensive movie website about movie posters, trailers, film reviews, news, reviews. We provide the latest and best movies and online film reviews, business cooperation or suggestions, please email us. (Copyright © 2017 - 2020 920MI)。EMAIL